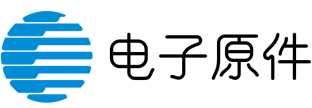 星空体育XK SPORTS(官方)APP下载IOS/Android通用版/手机app
星空体育XK SPORTS(官方)APP下载IOS/Android通用版/手机app
珐琅,经西域而来,听起来神秘而又浪漫,如“西域”一般神秘,像“法郎”一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称呼它为“搪瓷”,多了几分务实质朴,少了所有浪漫神秘。
笼统来讲,珐琅就是由多种矿物质组成的涂料,借能工巧匠之手或专业设备之力密着于器物之上,赋予后者或实用或靓丽的特点。当它叫搪瓷制品的时候,材料工程师会措辞严谨地描述它耐磨、硬度高、耐热、耐腐蚀、绝缘、有光泽……若它以精美珐琅器的面貌示人,观者将领略到明清珐琅工艺的辉煌。
当你面对博物馆典藏的一众珐琅珍品,耳边盘旋着讲解员一丝不苟的解说词,除了深感语言之于视觉震撼的无力,想必还可以学到几个专业表达——
如果以制作工艺给珐琅器分类,有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内填珐琅、画珐琅、口腔珐琅……
有图有真相,牙口真滴棒!上下两排齐整洁白,切牙(incisor)、尖牙(canine)、前磨牙(premolar)、磨牙(molar),这是你口中的32颗饮食利器,切咬叼嚼全靠它,冷热酸碱都不怕。
需要指出的是,这32颗牙里头有20颗经历过乳牙恒牙替换。通常来说,乳牙会在你三岁前长齐,六七岁时开始脱落。
牙齿在口腔内露出的部分叫牙冠,其表面是牙釉质,号称人体内最坚硬的组织;如上图所示,当我们把牙冠剖开,可以看到被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以及藏在牙本质里的牙髓。若将牙齿视作珐琅器,那么牙釉质就是珐琅,牙本质则为胎体。
“牙釉质”和“珐琅质”都译自英文单词“enamel”。Enamel一词形成于中世纪,被当时的西欧人用来指代“涂覆至金属或陶瓷等器具上的玻璃质材料”,也就是珐琅/搪瓷。(你也可以把它当动词用,意为“上釉”。)Enamel在法语中叫作“émail”。进入18世纪后,法国人开始用émail称呼“牙齿上最坚硬的部分”,即牙釉质;“enamel”也就逐渐多了这层含义。
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掀起一轮轮新思潮,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领域开始了革命,其中也包括牙科学。
1563年,人称“牙体解剖学之父”的意大利解剖学家巴托罗梅奥·埃乌斯塔基奥(Bartolomeo Eustachio)在其开宗之作《牙齿小书》(Libellus de Dentibus)[4]中介绍了牙本质和牙釉质,并将它们比作“橡果和橡果的壳”。《牙齿小书》共有30个章节,记录了关于牙齿形态和功能的重要发现,被认为是第一本详解牙齿解剖结构和功能的专著。
列文虎克——如今以形容词的姿态风靡全网的荷兰最强观察者——曾于17世纪借助能放大数百倍的自制显微镜观察牙齿结构。1677年,这位与巴斯德共享“微生物学之父”美名的“显微镜教父”绘制了牙釉质的显微草图[5]。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观察并绘制牙釉质,不过他们各有各的叫法,例如显微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双料祖师爷、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切罗·马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称牙釉质为“substantia filamentosa”(丝状物质),而在苏格兰牙医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口中,牙釉质名为“cortex striatus”(线]。
罗伯特·布莱克绘制的大象臼齿切片,字母e代表cortex striatus,即牙釉质。[5]
牙釉质成分的95%以上都是矿物质,其中以羟基磷灰石为主,氟磷灰石等为辅;它拥有号称仅次于金刚石的硬度,科学家发现牙釉质所承受的咀嚼压力与地壳压力共享同个测量尺度;它对冷热骤变和酸碱波动的忍耐力令人赞叹,它那洁白无瑕而又半透明的容颜更是无可指摘。
当然,口腔珐琅的工艺一点儿也不正统。它的制釉和上釉环节并不借助外力而是自主完成,它也不会经历高温焙烧——这听起来似乎少了点凤凰涅槃式的英雄色彩,但你如果真正了解牙釉质形成过程,或许会感受到那个微观生命世界的奇美。
在述说口腔珐琅的自我实现故事之前,我们需要花费一定笔墨介绍它的组织结构。
按照口腔组织学的定义,牙釉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是釉柱(enamel rod),数以百万计,呈细长柱状;釉柱横剖面则为锁眼形状,有一个较大的头部和一个细长的尾部。每条釉柱由数以百万计的磷灰石微晶组成。
一个釉尾的左右两侧挨着两个釉头。相邻的釉头釉尾间存在明显间隙,间隙内填充着釉柱间质(interrod substance/enamel cement)。柱间质成分当然也是微晶了,但其整体结构不如釉柱本身致密。柱间质构成的弧形边界被称为釉柱鞘(enamel rod sheath)。
釉柱从牙本质和牙釉质的分界面,即牙本质釉质界(dentinoenamel junction,简称DEJ),出发并贯穿至牙表面,但釉柱生长的行程并不完全呈直线的釉柱较直,称直釉;而靠内2/3的较弯曲,称绞釉(gnarled enamel)——尤其在切缘/牙尖部位,釉柱绞绕弯曲的情况更显著。
因此若只从形态层面讲,称绞釉为“釉条”似乎更妥当。(本文所用的几处示意图中,釉柱看起来好像全程都是直线,然而这并非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牙釉质不同部位的釉柱排列方式不尽相同。例如牙齿窝沟区域的釉柱是从DEJ出发,向窝沟底部集中,呈聚拢状;而靠近牙颈部的釉柱则大多水平排列。
大致了解牙釉质内部结构以后,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口腔珐琅的形成过程,就是以牙本质作胎体,向外生长无数条紧密排列的釉柱的过程。
普通珐琅的核心工艺是制釉、上釉、烧结这三大步,其中烧结的目的是让本为涂料形态的珐琅借助高温熔融并二次结晶,成为高质量晶体形态的珐琅层,同时与胎体紧密结合。
而在口腔珐琅中,作为釉料的羟基磷灰石从何而来呢?这些原料又是如何在无高温的情况下就长成晶体的呢?微晶为什么又会组成釉柱?这么多釉柱又为什么共同长成了牙釉质的独特结构形态?
没错,就是那些英文名叫“ameloblast”的神奇成釉细胞,那些扎根牙本质、仰望牙龈外的成釉细胞,那些能移动、善分泌、很“突出”的成釉细胞,那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成釉细胞。
当看到学者手绘的成釉细胞示意图时,多数外行很难相信这些用细腻笔触勾勒的粗粝图案会是细胞。
因为它们呈又细又长的柱状,横截面为六边形,而且相邻细胞无缝贴合,平行而立,这与我们印象里的细胞造型相差悬殊。
这些细胞“柱”的前身其实是短粗型的块状(在英文里可用“cuboidal”来形容),通过分化才长成了瘦高个儿。当然,关于它们此前如何猥琐发育,如何在牙本质界面上安营扎寨,如何做好“制釉”和“上釉”前的准备工作,纷繁往事暂且不表。
成釉细胞会分泌出特定基质。它们被称为牙釉质基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牙釉质的前驱体,由30%的羟基磷灰石,以及70%的“水分+蛋白质”组成。如上图所示,细胞的分泌活动在靠近牙本质的一端,也就是远离细胞核的一端进行;而且你明显可以看到,分泌端呈锥形突起,学者管这个叫“托姆斯突”(Tomes processes)。有凸自有凹,突起处分泌出的基质是带着凹坑的,有多少托姆斯突,就有多少“托姆斯突凹”(Tomes processes pits)。
托姆斯突兢兢业业地分泌基质,带凹坑的基质则越积越高,成釉细胞自然也跟着向高处迁移——它们如同一群建筑魔师,一砖一瓦脚下生,层层起楼步步高。
沉积的基质会持续吸收来自口腔(唾液等)的钙离子和磷酸根离子,生成矿物质晶体,与此同时又不断脱去蛋白质和水。如此一来,原本以有机物为核心的基质就逐步变作矿质含量高达96%的硬核牙釉质——数不尽的羟基磷灰石微晶正是由进入基质的矿物离子形成,微晶又组建出釉柱。
以上,便是前文所谓的“自主进行的制釉和上釉”,以及“不借助高温的结晶”。
当建筑魔师的造釉任务告一段落,成釉细胞将变回短粗的cuboidal形状,并与其他细胞结合形成鳞状上皮,暂时覆盖牙釉质表面,之后于牙冠萌出牙龈期间迁移至牙龈沟,最终悄然离开,可谓深藏功与名的典范。
这便是所谓科普写作黑色幽默的地方:当作者为了阐清“原理”、“机制”、“内核”实现他理想中的“硬核科普”,而堆砌一坨坨繁琐的细节描述,多数读者都会读得很蛋疼,并抱怨“我读这么一堆东西跟我捧一本教课书自学有什么区别?”若要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就必须献上“柔软而感性”的内容。显然,“牙釉质形成机制简述”不在其列。
作为写作者的我总会在“提供干货知识”和“增强文章可读性”之间被反复撕扯,并始终找不到答案,进而产生比读者更深切的蛋疼感,以及无力感。
那种无力感就好像,把千倍显微镜头下的牙釉质断面摆到你眼前,你看到釉柱的丛林繁密无尽,深不可测,想要穿过它,却又预感找不到尽头……
直到你发现断面上竟刻着一道道环线,犹如鸟瞰视角下的一条条林间甬道。你感觉新奇,便向那甬道走去,走进釉柱丛林,进入环线深处,那里竟别有洞天。
牙釉质上留存着两个尺度的时间线,每天增加一圈的横纹,以及每5~20天多一轮的生长线(又名芮氏线)。前者是釉柱增长拔高过程的直接标志,格局虽小,却直观详尽地记录了釉柱的纵向生长;芮氏线则视野更阔,以更长的周期标记着牙釉质在横向、纵向两个维度上的整体生长,是釉质发展前沿遭遇“中断期”时的见证。
如前所述,釉柱生长取决于成釉细胞分泌基质,而细胞活动又具有周期性,因此釉柱的长高过程(或者称釉质的纵向发展)也有周期性,并会留下周期标记。
在一昼夜的周期内,成釉细胞会经历快速分泌和缓慢分泌的阶段;由于内部微晶取向问题,釉柱在快分泌阶段越长越粗,在慢分泌时段越生越细,因此在快→慢的转折点,釉柱最粗,慢→快的临界处,釉柱最细。每过24小时,釉柱增加一个最细圈和一个最粗圈。
柱子上的最细圈从远处看,就是一条深色的线;许多根柱子平行而立,你自然会看到那些深色线条组合出的别样纹理——显微镜下的有规律横纹便是这样呈现的。它们反映釉质的纵向生长节律。(需注意,横纹和生长线都存在于牙釉质内部,只能在釉质断面上观察到。)
关于生长线(Retzius lines),学界对其形成机制仍不甚明了,但目前能确定的是它代表釉质发育前沿的大幅降速/中断,记录釉质生长史的中断期。
釉质形成始于牙尖点,向周围区域扩散,进而覆盖整个牙冠。换言之,不同区域成釉细胞的发育和分泌是有先后的,釉柱生长自然也有先后,牙尖处长得最早,越远离牙尖点的区域长得越晚。
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搁置纵向维度,只关注釉质的横向扩张,并其理想化为一个圆的扩增——以牙尖点为圆心,向外展开,半径越长的圆周越晚形成,最晚形成的最外层圆周,对应釉质刚好覆盖整个牙冠的那一圈。(同一半径圆周上的釉质可以看成是同时形成的。)
由于某些原因,在某些时段,原本活跃的成釉细胞会突然放慢甚至暂停其分泌活动,釉质的横向发展速率变得很慢,用某些学者的话说,“釉质的发育前沿改变了,形成的微晶取向不同寻常”。这种静止时段周期性出现,每次出现都会留下印记,也就是生长线。
在显微镜下观察牙釉质的横断面,你可以看到一圈圈深褐色的同心圆,好像树的年轮。通过这些年轮,研究者能精确检索中断期;而你如果点开这些中断期,或许会看到年轮主人的斑驳往事。
科学家们对于生长线有这样一个共识:越粗实的釉质生长线,意味着越严重的生长中断期,越显著的中断,意味着人体经历越大的压力。也正鉴于此,很多学者会把某些“浓重”的生长线称作压力线。
形成于胎儿出生阶段的新生线(neonatal line)是最浓重,也最具科学意义的压力线,因为出娘胎这件事之于牙釉质生长可谓超级压力源,而新生线不仅能被作为个体出生前后的分界,还给研究者提供了追溯母亲孕期压力史的参考。
精神病流行病学家艾琳·邓恩(Erin Dunn)曾与同事研究来自70个5-7岁儿童的70颗自然脱落乳牙的形貌[12],旨在关联“母亲孕期的精神压力”和“生长线的粗细”。
分析结果显示,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母亲所诞下的孩子医疗器械企业,其牙釉质的新生线往往更粗;而精神状况理想的母亲则更有可能孕育新生线更细的后代。这里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怀孕32周时的精神萎靡、重度抑郁以及焦虑症等精神疾病史。邓恩等人在控制了肥胖、母亲年龄和孕期服用补充剂等因素后,发现此相关性依然成立。
任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邓恩自号“科学牙仙”(the science tooth fairy),是乳牙重度发烧友,长期投身于劝导无知孩童捐赠乳牙的事业,白嫖而来的乳牙则交由其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牙齿发育专家菲利西塔斯·比德拉克(Felicitas Bidlack)。后者化身列文虎克女孩,考察每一颗乳牙的每一处凹槽、缺口和裂缝,使用X射线和CT扫描探察其内部结构,测量牙釉质厚度与矿物质密度,将它们切成一层层薄片并以显微镜观察……
2019年末,邓恩和比德拉克开启一项颇具野心的计划[15]。她们招募数百名以不同形式“目睹”过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且于此事件前后怀孕分娩的母亲及其孩子,收集来自这些儿童的乳牙,然后借助医疗记录解析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压力线。这里的“目睹”形式包括案发现场亲眼见证、电视收看实时新闻,或者在案发地区长期生活工作等。另外,她们设置了一个未目睹爆炸的对照组,对照组的乳牙样本来自观察组儿童的兄姐。
用比德拉克的话说,“如果最终事实证明爆炸案前后孕育的孩子的确有着断裂线更深的釉质,那将是令人震惊的结果。”[16]
在邓恩和比德拉克眼中,小小的乳牙釉质就是小小的生命档案,记录着机体早期与环境物质的接触,关于压力事件的回忆,通过对这些档案里的深色线条的解码,我们可以遥望母亲分娩前的精神世界,追溯孩童幼年的心灵旅途。
8岁的诺拉·方(Nora Fong,左)参加了邓恩等人的研究项目。她的母亲安德莉亚·方(Andrea Fong,右)曾通过实时新闻消息跟踪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动态,并于几周后生下诺拉。(ERIN CLARK/GLOBE STAFF)[17]
“当我们经历强烈的精神体验或感受到强大压力源,身体会做出反应。应对创伤的反应势必以某种形式融入受伤者的生理机能。一些创伤能影响大脑发育,甚至于DNA处留下印记。牙齿当然也会记录下些什么。”
“牙釉质或许可以成为儿童创伤的生物标志物,帮助解决我们在童年逆境领域遇到的关键问题。”
“那条深黑的新生线标志着从子宫向世界的跨越。从新生线开始,之后形成的生长线记录牙釉质固定周期的生长;其中可能出现某些更粗更深的压力线,它们意味着釉质发育的中断,表明某些东西妨害了孩子。”
如前文所述,邓恩和比德拉克作为该领域的先锋,已经付诸实践的学术探索更多聚焦于母亲孕期的压力,而尚未提及婴孩出世后的创伤。不难想见,涉及儿童逆境的此类研究,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克服诸多方面的障碍,而且往往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
对待猴子可以不像春天般温暖。我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挑选出理想幼崽,可以将它们置于特定、受控的环境下圈养起来,可以给他们统一发放食物、实行长期监视、安排身体检查,可以在它们大腿处纹上身份编号,可以将它们的每一次受伤和生病都记录在案,可以把它们与母亲和其他社群成员分离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貌似也有不少人类经历过。)
环境医学专家克里斯汀·奥斯汀(Christine Austin)和生物人类学家谭雅·史密斯(Tanya Smith)“招募”了十来只圈养小猴,以上述方式调查了它们牙齿里的压力档案[19]。她们发现,小猴在离开母亲和社群期间,牙釉质内形成了细微的压力线。这一结果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眼中,牙釉质不只记录个体的际遇,我们还可以顺着那些深浅不一的时间线穿越几十甚至上百万年,窥见古人的生活。
我们有幸发现百万年前的化石,便以其新生线为起始,以死亡年龄为终点,以横纹与生长线为刻度,计算该名幼童的牙釉质发育速度,而牙釉质发育速度又是区别人类种属的重要参考。这种计算帮助我们做出推断:“最接近智人的发育(development)是在直立人出现后开始的。”[21]
他们吮吸母乳,同时也得到了母乳内的18O医疗器械企业、钙、钡、铅,后者富集于牙釉质,而严寒压力则令生长线愈加深沉。现代学者通过分析25万年前的尼人牙齿,对他们当时面临的气候环境和金属元素暴露情况,甚至是哺乳周期,有了粗略见解[22]。
古罗马的新生儿是脆弱的,娘胎外的世界是凶险的,更有无数胎儿死于分娩途中。
当考古学家谈论古罗马的死产率时,他们常会谈起新生线,因为只有活着离开母亲身体的婴儿才能拥有完整新生线。新生线深邃夺目,将产前和产后的牙釉质分泌割裂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份出生证明。当然,并非每个顺利诞下的孩子都有出生证明;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后不满7-10天便夭折,我们很可能观察不到他牙齿里的新生线,因为牙釉质基质的完全矿化需要时间,过早死亡可能使得新生线部分的釉质太过脆弱而随时间流失[23]。
研究者分析了12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乳牙,发现他们的牙齿发育比现代人类早得多。[24]
牙釉质,因成釉细胞而生,坚硬赛金刚石,持久历百万年。不过,作为读者的你大可不必去深究它为何“硬而久”,因为“深究”比“阅读”更容易让你“软而快”(探索科学的意志变得疲软,研究事物的兴趣消失得很快)。实际上,只要读者能坚持看到这里,那么坚持写到这里的笔者便已露出疲软而欣慰的笑容。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医疗器械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医疗器械企业
